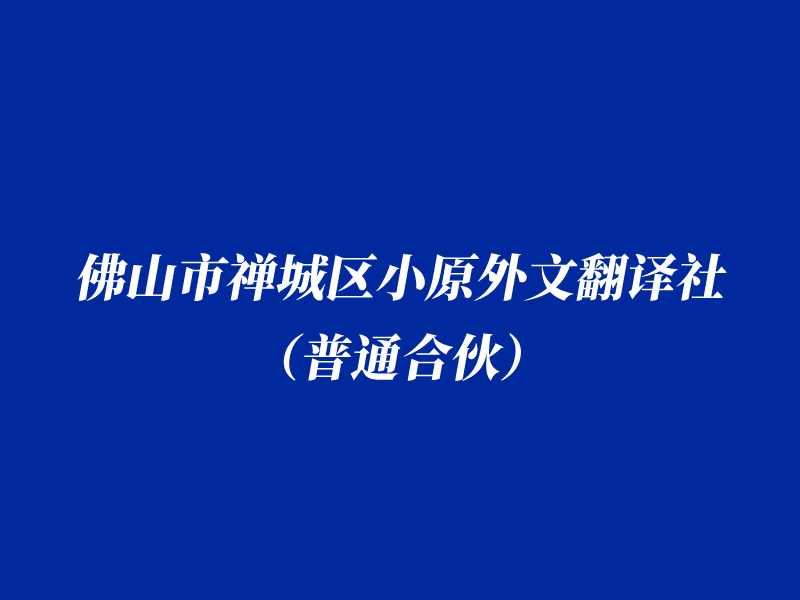Nov
2020
有不少朋友想做翻译,又不了解情况,经常会问我关于翻译的问题:翻译好不好做,会不会有什么困难,等等。我虽然**近几年没有翻译过书了,但基于之前积攒的经验,还是可以给出明确建议:翻译难做。
这条建议时常会遇到质疑。许多朋友会说:我虽然没有做过翻译,但我看英文没啥问题。翻译,不就是看懂英文转换成中文嘛。为什么你说那么难?
这么说的人,往往没有译者体验,只有读者体验,所以翻译无非是让读者从“读原文”变成“读译文”。如果真的当过译者,翻译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起码,下面几大困难是任何译者都躲不掉的。
60%覆盖不了30%
据我观察,普通人读一本书,充其量只看懂了全书内容的30%。许多时候甚至连30%都不到,**后有印象的只有一些有趣的故事、结论。叙事文本中大段的铺垫、描摹,说理文本中大量的论证、辨析,往往被读者所厌烦,好一点的也是一带而过。
这并不是读者不想多读一点,多懂一点。对大多数读者来说,要再多看懂一点、多理解一点,花的时间要大大增加。大家可以回忆中学的古文课,大学的经典阅读课,老师带着大家逐字逐句地阅读、解释,既消耗精力,记住的也不多。不只文学文本是这样,说理文本也是这样。记住结论相当简单,记住推理过程则麻烦许多,能自己复原整个推理过程,对一般读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挑战。
我们没法强迫读者花更多工夫,因为如何读、读懂多少,这是读者的权利。但是译者的责任不同,译者的理解范围往往是读者理解范围的上限。译者看不懂推理、搞不清辨析,只能囫囵吞枣硬译。读者读到这段诘屈聱牙、支离破碎的译文,只会觉得莫名其妙,未必能得出结论。
为了让译文读者的收获水平和原文读者保持相同,译者不得不花大量的功夫,加深自己对原文的理解。所以身为译者,许多文字不是“一路看过去”就好,而是必须反复推敲、琢磨。
比如这么个句子:“完整交互总共需要传输100K的数据,目前已经传输了50K,所以要关心的只有50K数据”。普通读者或许不觉得有问题,或者根本留意不到歧义,译者却必须搞清楚,后一个“50K”到底是“已经传输的50K”,还是“剩下没有传输的50K”,否则肯定会有部分读者有困惑。
这类问题只有一部分可以通过阅读上下文来判断,还有相当部分是不能靠上下文来猜测的。运气好的,可以直接联系原作者询问。运气不好的,就只能自己瞎蒙了。这样一个“无关紧要”的问题,往往就要消耗译者大量的时间。
还有一类问题,估计是译者怎么努力也“理解”不了的。我在《程序员身上的异味,你会直接告诉他吗?》中提到过,在我翻译《成为技术领导者》的时候,我虽然能这段文字翻译出来,但根本不理解作者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什么,为什么“告诉程序员他手上有异味”会成为一个问题。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段译文,虽然逐字逐句挑不出太多毛病,但我没理解,所以译文其实不通透。
更麻烦的是,即便译者花费了大量时间,把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提升到了60%,读者也可能根本感受不到。因为不同的读者所理解理解的30%各不相同。运气好的,读者的理解是译者理解的子集。运气不好的,读者的理解是译者的理解没有交集。
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争执:读者说译本很烂,译者感到委屈,自己已经花费了很多心力了,读者只抓住几处疏漏发难。背后的原理就在这里:译者费尽心思得到的那60%,完全盖不住读者的30%。
60%覆盖不了30%,这是译者的无奈,也是译者必须面对的挑战。
一支笔画不出百样色彩
即便译者倾尽全力,**理解了原文,仍然会让读者不满意,因为译文剥夺了读者的“解释权”。
什么是读者的解释权?简单说,就是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”。原文里怎么写的,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和想象,大家都有按照自己的体验、经验、想象去理解原文的权利。
译者却不同,译者首先是读者,他对原文当然有自己的理解,这是作读者的权利。另一方面,译文的那“一千个读者”仍然期望看到一千个汉姆雷特。然而这时候,译者的理解已经熔铸在翻译里,印刻在译文中,针对原文的众多解释和想象就此消失了。挑剔的读者,尤其是能读原文的读者,往往会感到不满意。
仍然举上面那段“传输数据”的文本的例子。在我看来,可能产生误解的根源在于原作者举例时不够仔细。如果我是作者,我不会说“完整交互总共需要传输100K的数据,目前已经传输了50K,所以要关心的只有50K数据”,而是改为“完整交互总共需要传输100K的数据,目前已经传输了60K,所以要关心的只有40K数据”,避免出现误解。
但只有身为作者,这种改动才可以理直气壮,译者没有百分百的理由和权利去修改原文。对这样的修改,许多读者并不买账,因为它“不忠于原文”。
我在讲翻译时曾写过,英文里的许多a其实只是语法需要,一律翻译成“一个”反而显得累赘。比如“每个地方都有一位负责的人,一个县应当有一位县长,一个市应当有一位市长,一个省应当有一位省长”就很累赘,地道的说法是“每个地方都有个负责人,县有县长,市有市长,省有省长”。
觉得没问题,对吧?我们看看更复杂的例子:“他好像一个独翼的天使,矗立在一张门前,死死盯住远方的一棵树”。按照上面的逻辑,更好的翻译似乎是这样的:“他好似独翼的天使,矗立门前,死死盯住远方的树”。
这个例子得到不少人的赞同,但也有不只一人反对,理由是“原文里连续出现的a,原作者应当是有特别用意,要表达孤单的感觉,一律去掉,反而改变了原文的韵味”。这种说法有道理吗?不好说完全没有道理。但是严格照原文翻译也有不少读者反对,理由是过多的“一个”完全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。
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译者,而在翻译。毕竟,原文的解释和想象的权利完全属于原文读者,一旦进入翻译,就必然剥夺一些针对原文的解释和想象。同样一段文字,你看来平淡无奇,我觉得微言大义,他认为别有所指。这种分别很微妙,较真就容易吵起来。但是,又没有绝对的、客观的对错标准,因为个人的理解本来就可以不同。所以文艺理论才会说,作品一旦写成,它就与作者脱钩,完全存在于读者的理解和阐释之中。
鲁迅先生写过: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,一棵是枣树,另一棵也是枣树。为什么要这么写?为什么不直接说“两颗都是枣树”?这些问题历来争论不休,不同人有不同理解。我估计就是鲁迅先生再世,未必也能给出大家信服的答案。译者如果遇到这种句子,无论怎么翻译,都得不到全部读者的认同。
一支笔画不出百样色彩,这始终无解的难题,是译者的宿命。
一张口难吃百家饭
“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汉姆雷特”,说的是读者的理解各异。其实除去读者的理解,原文涉及的领域也可能包罗万象。同样的概念,在一千个领域可能有一千种名称。不了解领域的行话,给不出“接地气”的说法,就会给读者感觉“出戏”、“外行”,这也是译者面临的难题。
比如specification,IT领域通常翻译为“参数指标”,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涉及到某些工业领域,就必须摇身一变,行话叫“规格说明”。具体到军工系统、武器制造,又得改头换面,叫做“性能诸元”。如果译者不了解这些,造出“火炮性能参数”,或者“软件系统规格”,读者就容易有意见。
再比如range,一般翻译为“范围”。但在IT领域,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就要翻译为“近距离通讯”,进入武器系统,short range missle就要翻译为“短程导弹”,交战中的in range更是应当翻译为“进入射程(已在射程内)”。
实际上,在翻译中类似的讲究很多,而且这类讲究没有固定规章可循,全凭译者平时留意。
比如-ist,一般说的“xx主义者”没错,但涉及到政局便有不同。“议会中的国际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各占半数”就明显别扭,符合习惯的翻译是“议会中的国际派和本土派各占半数”。还有international community,翻译为“国际社群”会笑掉大牙,约定俗成的翻译是“国际社会”,虽然community似乎和society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哪个人告诉你-ist翻译为“派”,哪本书告诉你community翻译为“社会”?没有,全靠译者平时用心,吃百家饭。如果没吃过百家饭,译文不自然、不地道就是必然的结果。我之前翻译《精通正则表达式》就吃过亏。
《精通正则表达式》的作者是美国人,大概美国人都对车很了解,所以原作者在讲解“水面下”的正则表达式匹配原理时,大量使用了汽车的例子:打开引擎盖,这里是分电盘,那里是变速箱……。
可惜,等我能把发动机舱里的东西都分得清楚,是交稿两年之后的事情了。在翻译的时候完全不熟悉车主们的行话,所以transmission到底翻译为“变速箱”还是“传动机构”,似乎总说“变速箱”也有点别扭…… 所以今天再看这段译文,虽然花了不少心思,还是不够地道。
不但国内有百家饭,国际上也有百家饭。我就见过译文里出现的“日本外交部长”。没错,foreign minister通常的翻译正是“外交部长”,“日本外交部长”干的确实是“外交部长”的活。但译者需要知道,在日本这个职位有专门的称呼,叫“外相”或“外务大臣”。由此类推,日本内阁的Chief Secretary也不是“秘书长”,而是“内阁官房长官”。
百家饭不只关系当下,还涉及历史。同样的概念,不同时代的称呼也不同。麻烦的是,一般词典并不会涉及“历史称呼”,所以更要靠译者平时留心。比如foreign affairs,如今大家都知道叫“外交事务”,往前倒推一百多年,晚清的说法是“洋务”,再往前几十年,就得叫“夷务”。不懂得这些,译文就会显得跳脱、错位。
译者怎么能懂得各种领域的行话?没有太多好办法,只能平时自己多留意,把各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起来。
美在你心中
毫无疑问,在当今社会,翻译是个“辛苦而不赚钱”的活。翻译的稿酬,二十多年来始终停留在每千字60-80人民币。
我自己在状态**好的时候,翻译速度充其量也只有每小时一千字。这还不算上之前阅读、之后审校的时间。更要命的是,这样的“神勇状态”,一天充其量只能维持2-3小时,维持这2-3小时的代价是整天疲惫不堪。
辛苦而不赚钱,更“奇怪”的是,不管翻译得好与不好,所得报酬几乎没有差别。所以,相当部分的译者选择了“体谅”自己,暗地里放松了对译文的要求。毕竟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,每个细节都要去抠,去苦苦思索,去反复推敲,实在得不偿失。许多“不妨碍理解的蹩脚译文”,也就此诞生。
什么是“不妨碍理解的蹩脚译文”?就是表达很奇怪,虽然明白意思,但读来总觉得别扭。上文已经举了若干例子,不过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。
比如“他朝飞机发射了三颗子弹”。简直可以从译文里直接看到原文:He fired 3 bullets to the plane。能看懂吗?能看懂。别扭吗?别扭。那么不别扭的说法是什么?仔细想想,应该是“他朝飞机开了三枪”。为什么不容易想到,因为语言不通,描述同样现象的认知角度不同。
再比如“他个子不高,大家都叫他‘小人汤姆’”。能看懂吗?大概能看懂,说的是体格小巧。别扭吗?别扭。虽然有“小人国”的说法,但“小人”单独出现,通常是指品格不高尚,用来形容体格就显得挺怪异。那么不别扭的说法是什么?仔细想想,“小个儿汤姆”就顺口多了。
无论把“发射了三颗子弹”改为“开了三枪”,还是把“小人汤姆”改成“小个汤姆”,可能都免不了花工夫思量,而且收入多半不会增加,也不一定会得到特别的赏识。唯一的驱动力只能是译者内心对美的追求:这样是美的,那样是不美的,我们应该追求美,哪怕并没有现实的好处。
我只能找到“内心对美的追求”这个原因,尽管这或许是对译者的苛责。普通人说话写文章,错就错了,甚至错着错着就成了约定俗称的表达。不信你搜搜看,现在有多少人把“义正辞(词)严”写成了“义正言词”,把“攻城掠地”写成了“攻城略地”。虽说相差十万八千里,形式、意思都乱套了,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日常使用。作者这么做大概无可苛责,译者却享受不了这种“特权”。
张大春先生曾写过《用字不妄》,讲的是虽然如今火星文发达,仍然有不少人向他请教,斟酌计较于字、词的选择,纠结于字词的细微差别。说话发帖不难,查字典也不难,字斟句酌所反映的,恐怕不是一个社会所能积聚的文字学专业素养,而是社会大众愿意讲究文字的意愿和好奇心。
“行路不难,只是辛苦。问路实难,它决定了旅程长远的价值”。好的译者,不该放弃内心对美的追求。
本文摘自网络
上一篇:做口译员的好处与挑战
下一篇:日语长句如何翻译?
- [03-27]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翻译教育的危机
- [10-31] 英汉翻译中常见的十大差异
- [02-17] 做好汉语乡土语言翻译 展现国内真实风土人情
- [01-15] 佛山翻译行业的规模是多少
- [10-22] 翻译文件的收费标准是什么?
- [03-23] 如何**本地化翻译的准确性
- [04-24] 初做翻译的几点建议
- [08-21] 日语特点和翻译技巧知多少

-
地址1: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144号科华大厦1002室(创业大厦正对面)
电话:0757-82285965 13318391728
-
地址2:佛山市禅城区魁奇路澜石(国际)金属交易中心大厅一楼
电话:0757-82285965 13318391728